世界古代各国都有刺字和文身的习俗,先在人身上刺字或图案,再涂以墨汁或其他色素,使之沉着于皮下组织,永不褪落。除刺字、文身而外,宋代还有簪花的习俗。
刺字
宋代继承前代习俗,在军人和大多数囚犯的面部或其他部位刺字。对于囚犯,是作为刑罚之一,北宋初仅适用于贷死的囚犯,此后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到大多数囚犯。至孝宗淳熙间,刺配法增至570条。神宗末年,重定黥配法,规定“犯盗,刺环于耳后;徒、流以方,杖以圆。三犯杖,移于面,径不得过五分”。刺面分为大刺与小刺两种。凡被认为“情重凶恶”的囚犯,所刺之字稍大,两面分刺。仁宗赞成只刺一面,字样可稍大。所刺文字,如囚犯被判流罪,命刺其面为“刺配某州牢城”。如果罪不至此,量刑过重,则在这些字前加“特”字。高宗、孝宗时,对宽大处理给予“贷命”的“强盗”,在额上刺“强盗”二字,在脸上刺大字“配某州或某府重役”,或“配某州、府屯驻军重役”。如被宽大处理的“强盗”而可充兵,则在额上刺“免斩”二字,在“面刺双旗”。
北宋还继承前朝的习俗,凡招募士兵,皆在其面部刺上小字,“各识军号”。仁宗初年,规定在京东西、河北等路募兵,“当部送者刺‘指挥’二字”。庆历二年,选河北、河东强壮并抄民丁刺手背为“义勇”。康定间,又在环、庆二州以沿边弓手“涅手背充”寨户。英宗治平元年(1064年),再次在陕西点义勇,“止涅手背”。神宗熙宁七年(1074年),在河北招募蕃人弓箭手,“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‘蕃兵’二字”。钦宗靖康元年(1126年),朝廷拟在陕西路招募“义勇”,“止于右臂上刺字”。南宋时,士兵仍然免不了在额部和手背刺字。方回记载说,当时“大军刺字,号以姓名;禁、厢军刺额,号以六点”。额部一般刺军号,手部一般刺姓名。
有些军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志向,也在自己身体上刺字。如北宋时,兵马副部署、保州刺史呼延赞在自己身上刺“赤心杀贼”四字,表示“愿死于贼”。岳飞背上刺有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,“深入肤理”,相传是岳飞的母亲亲自替他刺上的。高宗初年,抗金名将王彦退入太行山,聚集义军。为表示抗敌的决心,义军皆面刺“赤心报国,誓杀金贼”八字,号称“八字军”,河北、河东百姓纷纷响应。
金朝奴婢的面部或身上往往刺字,对此朝廷一般不予过问。宋金战争之初,金军统帅完颜宗翰(粘罕)命令各地大量捉拿中原民众,将他们没为奴婢,在这些奴婢“耳上刺‘官’字”,先“散养民间”,再“立价卖之”。南宋使者范成大在金朝亲眼看到奴婢“两颊刺‘逃走’二字”,系“主家私自黥涅”。其《清远店》诗云:“屠婢杀奴官不问,大书黥面罚犹轻。”而宋朝则禁止主人私自黥刺奴仆。宋英宗时,官员刘注被“追三官,潭州编管”,其罪状之一便是“刺仆人面,为‘逃走’二字”。
文身
宋代有些市井百姓喜欢文身,称为“刺绣”。迎神的团体称“锦体社”。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称“针笔匠”,他们往往“设肆为业”。荆州的街子葛清,自头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诗和画:“不是此花偏爱菊”句,刺“则有一人持杯,临菊丛”图,“黄夹缬林寒有叶”句,刺“一树上挂缬”图。共刺20多处,人们称他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。宋太祖、太宗时,有“拣停军人”张花项,晚年出家做道士。当时习俗“以其项多雕篆”,所以“目之为‘花项’”。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,年轻气盛,行为“不检”,“文其身”,被赐号“锦体谪仙”。东京百姓在大街上庆祝重大节日时,“少年狎客”往往追随在妓女队伍之后,也“跨马轻衫小帽”,另由三五名文身的“恶少年”“控马”,称“花腿”。所谓花腿,乃自臀而下,纹刺至足。东京“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”。南宋初,张俊所率军队常驻“行在”,挑选少壮长大的士兵皆刺花腿,防止逃往其他军队,“用为验也”。孝宗、宁宗时,饶州百姓朱三的“臂、股、胸、背皆刺文绣”;鄱阳东湖阳步村民吴六也“满身雕青”;吉州太和居民谢六“举体雕青,故人目为‘花六’,自称青狮子”。理宗淳祐以后,临安有名的店铺中有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,其店主人显然也是刺双腿者。现存宋人画杂剧《卖眼药》绢画中,绘有一位手臂“点青”的市民(图一)。但朝廷严禁宗室“雕青”。

图一 南宋佚名 《杂剧卖眼药图》 故宫博物院藏
由于不少南方少数民族系古代越人的后裔,他们直到宋代仍保留文身的习俗,如《清波杂志》卷10称:广南黎洞“人皆文身,男女同浴”,以致有“文身及老幼,川浴女同男”之说。但又各有其特点,壮族先民只有女奴婢才黥面。《岭外代答》卷10《绣面》称“邕州溪峒使女,惧其逃亡,则黥其面”。而黎女绣面属于“吉礼”,《诸蕃志》卷下《黎》云:“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,谓之绣面。女既黥,集亲客相贺庆,惟婢获则不绣面。”黎族先民只有女性才绣面,而金齿蛮则男性与女性皆文身,并因此有绣面蛮、花脚蛮一类的称呼。《云南志略·诸蛮风俗》称:“文其面者,谓之绣面蛮;绣其足者,谓之花脚蛮。”《马可波罗行纪·金齿州下》说:“男子刺黑线纹于臂腿下。刺之法,结五针为一束,刺肉出血,然后用一种黑色颜料擦其上,既擦,永不磨灭。此种黑线,为一种装饰,并为一种区别标识。”
簪花
宋代沿袭前朝习俗,不论社会地位或性别、年龄,在平时或节日,都簪戴花朵(图二)。

图二 宋佚名《宋仁宗后坐像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从宋初起,逐步形成“故事”:凡大臣参加皇帝举办的宴会,皆赐给宫中名花,其中亲王和宰臣由内侍将花插在他们的幞头上,其他官员自己戴花。皇帝有时也特命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戴花,使旁观的官员们羡慕不已。每年三月,皇帝与大臣们赴金明池游玩,从宰相到从臣,都赐“生花”即鲜花,“皆簪花而归”。这些花朵分为三品:凡遇圣节大宴,如有辽朝使臣参加,则用绢帛做花,“示之以礼俭”。春、秋季的两次宴会,则用罗帛做花,“为甚美丽”。至于大礼后恭谢、上元游春等,从臣都随皇帝出行,到时安排小宴称为“对御”。凡遇“对御”,即赐从臣们“滴粉缕金花”,“极其珍巧矣”。在赐给从臣们“燕花”时,一般按照官员的品阶决定多少,而在赐给滴粉缕金花时,数量则比平常加倍。这些花朵因为是皇帝赐给的,所以又称“御花”,大臣们遇到这种场合都要穿“公裳,簪御花”。花朵一般都插在幞头上,所以又称“簪戴”。
宋朝皇帝每逢重要庆典,也簪戴花朵。如真宗时,曾特赐东京留守陈尧叟和大内都巡检使马知节御宴,“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花而行”。在宴会中,真宗命陈尧叟“尽去所戴者”,“召近御座,真宗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,陈跪受拜舞谢”。徽宗每次出游,回宫时则“御裹小帽,簪花,乘马”。同时,对“前后从驾臣僚、百司仪卫,悉赐花”。南宋时,官员们每逢重要节庆,如郊祀、明堂礼毕回銮、圣节、赐宴时,都在幞头簪花。花朵分为三种,一为大罗花,分为红、黄、银红三种颜色;二为栾枝即双枝,用各种颜色的罗制成;三为大绢花,分为红、银红两种。罗花以赐百官,栾枝赐卿、监以上官员,绢花赐将校以下武官。各级官员所戴花朵有一定的数量,不准随便超过限数(图三)。

图三 南宋佚名《田畯醉归图》(局部) 故宫博物院藏
宋代官民所戴花朵,除上述罗花、绢花、滴粉缕金花外,还有真花即生花,以及用通草、琉璃制成的花朵。人们喜爱簪戴真花的著名地区有洛阳和扬州,《洛阳牡丹记》说:洛阳之俗“大抵好花,春时,城中无贵贱皆插花,虽负担者亦然”。扬州居民与洛阳“无异”,“无贵贱皆喜戴花”。这两地居民所戴之花大都是真正的牡丹和芍药。当然,洛阳居民也有戴仿生花朵的。如宋太祖开宝初年,洛阳有李姓染匠,又“能打装花缬”,人们称之为“李装花”。这种仿生花朵使用罗、绢为材料。此外,还有用通草和琉璃即玻璃制作花朵的。如宁宗时,饶州一户居民以生产通草花朵为业。度宗时,宫中流行簪戴琉璃花,因此“都下人争效之”。当时,临安有人赋诗道:“京城禁珠翠,天下尽琉璃。”“识者以为流离之兆。”
南宋临安的414行中,有面花儿行或花朵市、花团。著名的花市或花团在官巷,官巷内著名的花铺有齐家、归家花朵铺,它们专门生产和销售各种花朵,其中有“像生花朵”、“罗帛脱蜡像生四时小枝花朵”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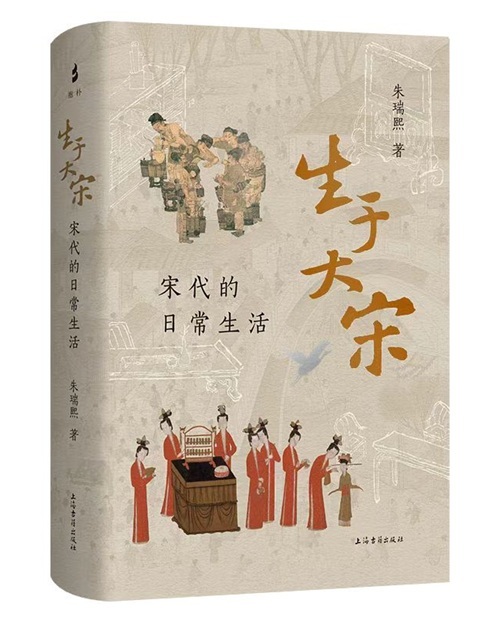
本文摘自《生于大宋:宋代的日常生活》,朱瑞熙著,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。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小橙子的城堡,本文标题:《宋代的刺字、文身和簪花》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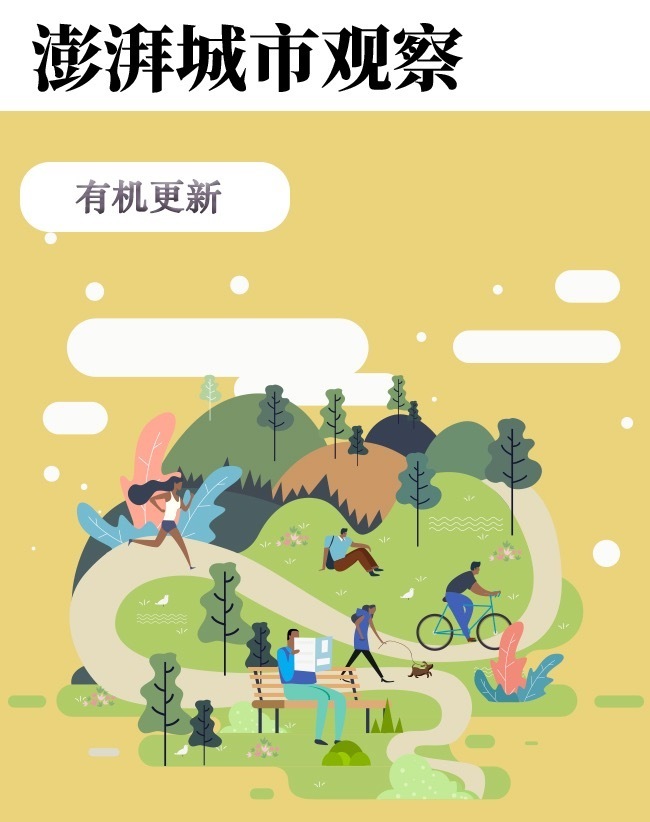

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津ICP备2021005108号-1
津ICP备2021005108号-1